1987年,我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,留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,单位在新源里西一楼,离“长城饭店”不远(自行车10分钟),偶因朋友介绍,去“替补”弹钢琴,不免动了干下去的心思。两小时30元的报酬,在当时可是令人羡慕、又干净又高雅的活儿。刚毕业,得想法养活自己。收入过低的音乐家个个都渴望靠手艺“挣外快”,所以“饭店乐师”早被驻京院团瓜分了。想占一席之地,就得自我牺牲,适应捷足先登者的要求,在人家不愿干的时段,插进一只脚,慢慢扩大地盘。所以,人家一旦有公事,我就“替补”。时间一长,自然混熟了,位置慢慢固定下来,这与陕北乡村的“吹手”挤着“拉活儿”争地盘一样。后来不单长城饭店,昆仑饭店、长富宫饭店、新世纪饭店、京伦饭店、北京饭店、建国饭店,几乎都建立了联系,地盘越占越大。人脉熟络了,自然机会多。空间的开拓,使我结识了圈内的大部分乐师,接到电话,绝对诚信,救场如救火嘛。自己置办了一套演出服,到哪儿都用得上。
实在说来,饭店“找活儿”的另一原因,是我所住的“筒子楼”无法洗澡。到饭店弹琴,可以享受员工待遇,在楼下更衣处,换演出服时,顺便洗个澡。当时,这是很奢侈也很吸引人的实惠。
别人不愿意干的时段,我都毫不迟疑地接受。按长城饭店“茶园”的时间表,下午4点至6点,钢琴弹两小时。6点至10点,客人最多的黄金时段,钢琴一小时,弦乐四重奏一小时,轮流换班。晚上10点到12点,钢琴两小时糖心。最好时段自然是6点到10点,一小时一换,既不累还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吃饭洗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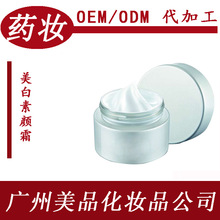
一年之中最没人干的时段自然是春节,特别“大年三十”。虽说收入翻倍,但对于中国人来说,除夕夜团圆,不是钱的事儿。初来乍到,为了立足,我答应了所有乐师提出的从下午6点到晚上12点的“全活儿”。虽然饭店管理者不允许这样做,但找不到人,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就是那个除夕夜,我体会到乐师为了生计不得不忍受长时间折磨的痛苦。六个小时!体力和心力的承受极限。越到最后,越难忍受,每分钟都变得如此之长,不免想到爱因斯坦“相对论”的比喻:“与情人坐在一起,一小时像一分钟一样短;坐在火炉子上,一分钟像一小时一样长”。那是坐在炉子上,炙烤屁股,如坐针毡,度日如年。不能忍受时,就鼓励自己,一个晚上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,咬着牙也要坚持!新年的钟声,终于敲响了,我弹完了最后一个忧郁而孤独的音符。扣上琴盖,飞一般逃离饭店。外面已是爆竹漫天了。
后来到乡村采访,了解到陕北的“吹手”、晋北的“鼓匠”都不把乐器称为“乐器”而称为“家具”。开始也不知道何以如此称呼的原因。当我沉下心来,试图解释其中原委时,突然想起了那个难熬的除夕夜。于是,语义豁然开朗,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陕北的“吹手”、晋北的“鼓匠”不把乐器称“乐器”而称为“家具”的原因。
对于演奏者,手中的“家伙”实在不是获得“快乐”的器物,而是养家糊口的“家具”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描绘过贝多芬童年被父亲逼着弹钢琴的经历。贝多芬痛恨折磨自己的“大机器”(被家长逼着学乐器的孩子大概都有同感),那件令“他人”愉悦的“乐器”,对演奏者来说,却如同“刑具”!
反过来推知,谁把“乐器”称为“乐器”呢?坐在山珍海味的餐桌前,听着锦瑟瑶琴,看着婀娜舞姿的王公贵戚!统治者才会把带来“快乐”的响器,称为“乐器”。作为欣赏者,视发出乐音的器物为“乐器”,自然是因为它们带来了快乐;作为演奏者,不称发出动静的器物为“乐器”,自然是因为没有带给自己快乐。这就是“局内人”“局外人”的立场。站在前者立场,自然是“乐器”;站在后者立场,自然是“家具”。这就是为什么先秦典籍《周礼》堂而皇之使用的名词,到了民间乐师口中会变为一点“诗意”也没有的原因!

陕北民间葬礼有个固定程序,称为“待饭”。即主家宴请所有前来捧场的客人吃饭的过程,也就是鼓匠、吹手一直要保持演奏直到全部仪式结束的过程。我在陕北参加了一个村庄的葬礼仪式,亲身感知了“待饭”过程。那是个极度贫穷的小村庄,因为平常在炕几上吃饭,全村能找到的桌子只有四张,全部搬到事主院中。一桌八人,四八三十二,一次只能坐下三十来口子。邻里乡亲一百六十多号,轮番排队。一道道盘子呈上来,一道道盘子撤下去;一盅盅琼浆品过来,一罐罐空瓶拿下去;一拨拨客人坐上来,一拨拨客人换下去。整个过程,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。无须说,“待饭”对于吹手来说,简直就是“施暴”。

对于漫长程序中吹手们的体验,当然是作为音乐家的我,在上述那个除夕夜的经历中体验到的。我所处的环境与吹手相比,相差何止十万八千倍。我坐在干干净净、环境优雅的“五星级饭店”,皮质松软的座登,中央空调的凉风,煞舌爽口的可乐(饭店每次提供两听),彬彬有礼的客人(时常报以掌声)。虽说六小时,但乐曲之间可稍事休息TXAPP.TV。即便身处如此环境,依然苦不堪言。那么,对于暴晒于“汗滴禾下土”的黄土高坡,坐在连棵树影都没有的硬邦邦的黄土地上,除了凉白开什么也没有,客人还时不时粗暴呵斥不能停顿,必须连续演奏两个小时的吹手来说,心里的滋味是什么?他们比我糟糕多少倍!马不停蹄、无间无隙、耗尽体力、摧残意志、无穷动、非人性地吹两小时唢呐,谁能承受?然而,对于陕北吹手来说,这是家常便饭!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仪式复仪式,待饭复待饭,直到吹不动为止。所以,他们怎会把手中的“家伙”文质彬彬、斯斯文文、软声款语地称为“乐器”而不实实在在、硬硬梆梆、直不笼统地称为“家具”?
“待饭”过程中,对于既享受美食又享受音乐的雇主,当然把乐器称为“乐”器,而看着别人细嚼慢咽而口舌生津的吹手,自然把乐器称为“家具”。任何事物,出发点不一样,叫法自然不同。这不是正式名称与俗称的区别,而是称呼者身份和立场的区别。对听众来说,这是享受;对音乐家来说,这是折磨。对享有者来说,金子是“美人首饰侯王印”;对“淘金女伴”来说,金子是“尽是沙中浪底来”。(刘禹锡《浪淘沙》)对于“不识渔家苦”的画家来说,自然是“好作寒江钓雪图”;对于“呵冻提篙手未苏”的“渔家”来说,确是“满船凉月雪模糊”。(明孙承宗《渔家》)
所以,观察一件事物的称呼,必须观察称呼者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的生存环境,而非仅仅看名称本身。这就是身为同一事物的乐器,之所以在一部分人口中称为“乐器”而在另一部分人口中称为“家具”的原因!
文/张振涛